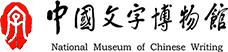2021年中国文字博物馆结项科研项目(课题)一览表
序号项目/课题名称类别合同编号负责人起止时间合同金额到款经费1甲骨文从水之字的研究及字形演变省级SKL-2020-831张怡2020.9-2021.9002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省级SKL-2020-1051辛春2020.9-2021.9003甲骨文中的“酉”与殷墟时期的玉柄形器省级SKL-2020-832张丽敏2020.9-2021.9004甲骨文的弘扬、传承与普及研究——以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例省级SKL-2020-933王双庆2020.9-2021.900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河南权威甲骨文数据库建设研究省级SKL-2020-1036魏文萃2020.9-2021.9006以甲骨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加深中华文化的传播省级SKL-2020-1164赵 涛2020.9-2021.9007中国文字博物馆临时展览十年回顾(2009-2019)省级SKL-2020-1208贺春辉2020.9-2021.9008黄河流域文化村落整体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以河南为例省级SKL-2020-987魏萌萌2020.9-2021.9009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提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研究市重点ASKG21010李宁2021.5-2021.90010加强“三农”工作统筹,推进全市乡村振兴总体工作布局研究 市重点ASKG21011张静宁2021.5-2021.90011充分挖掘甲骨文文化传承创新市级ASKG21047 付巍巍2021.5-2021.90012充分挖掘曹魏文化 打造文化旅游强市市级ASKG21043 赵娜2021.5-2021.90013推动社科工作者进军网络主战场对策研究市级ASKG21044 冯宇晓2021.5-2021.90014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以中国文字博物馆研学教育为例 市级ASKG21046 杨鑫2021.5-2021.90015弘扬安阳优秀传统文化 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市级ASKG21045 李瑞雪2021.5-2021.90016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市级ASKG21045 辛春2021.5-2021.90017文旅融合背景下安阳市博物馆研学实践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前景——以中国文字博物馆古文字研学实践教育为例市级ASKG21100 杨焱2021.5-2021.90018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市级ASKG21101 郝睿2021.5-2021.90019组、宾组与出组卜旬辞的流变 市级ASKG21098张怡2021.5-2021.90020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市级ASKG211207 韩洁2021.5-2021.90021浅谈如何提升博物馆讲解员讲解水平——以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例市级ASKG211206 徐耀2021.5-2021.90022安阳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市级ASKG211204 邢若飞2021.5-2021.90023挖掘安阳殷商文化 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市级ASKG211204 王华2021.5-2021.90024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安阳如何改变 “历史底蕴丰厚,休闲娱乐不足”的局面市级ASKG21367 种亚丹2021.5-2021.90025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安阳黄河文化的2发掘传承研究市级ASKG21364 李冰2021.5-2021.90026文旅融合背景下联合带动全域研学高质量高发展路径探析市级ASKG21363 尚峤2021.5-2021.90027关于我市知识产权保护、应用和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市级ASKG21365 陈瑞华2021.5-2021.90028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市级ASKG21366 张悦2021.5-2021.900
日期:[ 2021-12-14 ] 阅读:5675